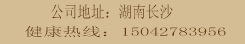周五睡下时已接近凌晨,身体早已疲乏但大脑似乎还有些兴奋所以睡得不太安稳。
感觉是在半梦半醒的状态听到了有人踩着楼梯发出“砰砰砰”的声音一下重一下轻的往楼上走来,我们家是loft的格局,我的睡房在二楼斜对着楼梯口,我一个人在家住时候我习惯都不关着睡房的门,我睡梦里隐约的看着有个不太高像一个女人的黑影从楼梯口缓缓的进到我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我的床沿上,我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床垫往下沉了一下。
我很想努力睁眼看一下是谁但就是不管怎么努力都睁不开眼。然后黑影就给我掖了掖被子,还捏捏我的脸颊笑着说:“以晶呀!都大丫头了还依然踢被子,没事!睡吧我就是来看看你,我回去了”。说着床垫往回弹了一下就看见一个背影又缓缓的朝楼梯口走去,始终我都没看清这背影是谁。
我瞬间梦里惊醒,扭亮床头灯拿起手机一看是凌晨两点半。
我坐在床上一阵恍惚刚刚发生了什么?是梦吗?可是醒来后留在脸上那种的触感又好真实,仿佛还有余温,刚刚捏我脸颊那双手是粗糙又冰凉的。我起身下楼想看看是不是家里的进户门没关,刚真有人来过吗?我甚至脑子里还觉得刚这个黑影可能还没走远,得追出去看一看。所以我穿着睡衣脱鞋顶着睡成乱七八糟的头发从27楼到一楼,还在小区里逛了半圈四处搜寻企图寻找到这个陌生又带点熟悉的黑影。也许是凌晨的风有点清凉吧,在一阵夹带着香泡树香味的凉风吹来,我打了一激灵,人瞬间也清醒了很多。我看了看周围一片安静,只有不远处那昏黄的路灯下有一只野猫在茫然的漫步,我有点好奇它是否跟我一样因为睡梦里被惊醒而内心不安在这寂静的夜里寻求答案呢。如果是人就好了,我一定会去拉上他去喝两杯排解一下刚才这个迷梦带来的恍惚。在低头看了一下路灯把我拉长的倒影,呵……还好四周没人,这像雄狮一样张扬的发型,睡裤裤腿一脚高一脚低怎么看都像疯子,拔腿快步的走回电梯。
回到了家里坐在沙发上了喝了一杯水,这一通折腾,人已经毫无睡意。坐在沙发上发呆等天明。
清晨想去小区对面的“知味观”吃点早餐,穿马路在等红绿灯时候望着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高楼突然有种压抑逼仄得透不过气来感觉,对耳边的喧嚣也很焦躁想立马逃离。就想去一个风景如画又闹中取静的地方去逛逛。所以吃好早餐就一个人背着包离开杭州去了上海的枫泾古镇。
接到妈妈电话那会我正在小河边的一只乌篷船上逗弄鸬鹚玩得不亦乐乎满脸愉悦。看到电话提示是老母亲来电正想分享这好玩的鸬鹚给她,却听到妈妈在电话里语气哽咽的说:“囡囡,你阿凤妗妗昨天十二点多吊死在自己家的厨房了,听你外婆讲白天的时候她还拿了水果和一袋子自己手工磨的小米粉来过你老外婆家的,谁曾想..........”
这恍如晴天的一个炸雷,我脑子出现了短暂的空白,踉跄了一下一屁股跌坐在了乌篷船的船尾上。惊得站在船尾的几只鸬鹚一只只慌张的跃入水里。等反应过来已经半个小时后了,泪如开了闸的水库一泄而下。那个睡梦里熟悉又陌生的背影不正是这两年阿凤妗妗帕金森发作时候的样子么,她原来是来跟我告别了。我好懊悔我当时没有认出她,梦里我还有点恐惧。
我买了去外婆家的高铁,坐在车厢里望着窗外铁轨旁笔直的电线杆呼啸着倒退,心潮起伏。回忆在一帧一帧的跳动,心里如同有一座冰山,在火堆旁烤着一时暖暖的,一时又透着刺骨的寒意。一个人到底对这世间绝望到何等的地步,才会决然得选择如此惨烈方式谢幕。
两个小时候后下午三四点吧到了外婆家,外婆跟妈妈手里提着香烛跟黄纸早已经在村口等我汇合一起去阿凤妗妗家见最后一面,因为再晚点她该化为一缕青烟了。黄纸的颜色在阳光的照射下黄得是那么的刺眼。去阿凤妗妗家路上,外婆一路泪眼婆娑叨叨着:“怎么这么傻!怎么这么傻!”也在讲着一些阿凤对她的好,还不停的问我妈你还记得这些吗?
我妈不停点着都回答:“我记得,我记得”。
短短七八分钟的路程这母女两人哭了一路,用完了我一包手帕纸。
踏进阿凤家的院子,西屋的正中间用门板配着两条长凳搭起来的简易灵床上,阿凤盖着白布头朝外脚朝里的躺着,灵床下面齐整放着一双后跟已磨得很薄的黑色布鞋,它仿佛还有一丝余温沉默的、悲伤的听所有人的哭泣。屋子不大却显得那么空旷与凄凉。我掀开白布想见最后一眼,可是眼前的一幕还是让自己忍不住的闭上眼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是因为恐惧是心疼,白布下的阿凤脖子上一圈的乌紫,断了的喉骨导致嘴巴不能正常闭起,舌骨因受到了挤压舌头半露,面部因为静脉回血受阻而发青、发紫,眼球凸起,这脸已无半分昔日的模样,望一眼早已悲伤成河。胸前的衣襟上零星的几点油渍试图在努力安慰我,阿凤妗妗只是在午睡,但眼眶周边那暗紫的尸斑又讨厌的在提醒我要清醒——她永远的走了。我再也听不到那爽朗的笑声,也听不见她喊我:“囡囡,拿个碗到妗妗家装好吃的,红烧蹄髈熟了……”
外婆跟妈妈蹲在院中往火盆里边添烧着纸钱边喃喃私语低低抽泣。外婆想擦擦被烟熏与泪浸湿的眼角,余光中扫到我还站在灵床旁两手撑着白布的两角在吧嗒吧嗒的掉泪,她走到我身旁从我手里拿过白布的两角轻轻的盖回阿凤的脸上然后哽咽着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对阿凤说:“走吧!走吧!孩子走吧……”
随后外婆牵着我的手往院中走去,阿凤家的小儿媳从院门外进来端了三杯水,招呼我们喝水。我很想问一句:“为什么?不给我阿凤妗妗换件干净的衣服?”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这个小儿媳不孝顺村里早已传闻已久。活着的时候对婆婆都是恶语相向,人死后再所做的一切与哀伤那都是演给活人欣赏的折子戏。衣服干净与否,换与不换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
从阿凤妗妗家出来,我跟我妈一人一边搀扶着老太太往自家走去,我沉默不语因为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念头:如果说人的一生是颗秀逗糖,她显然已经尝尽了酸涩的外壳,到底是谁的苛责阻断了她通往甜蜜的那条路?
路过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几个老人在大树下话语家常,看我们仨走来,其中一个老太太拉开两张折叠凳,让我外婆跟我妈坐下歇一歇。
她叫娜婆婆,她原是阿凤妗妗还住老房子时的邻居。
待我外婆坐稳后她把椅子朝我外婆跟前挪了挪,拉着我外婆的手放在自己手掌心里轻轻的拍了几下说:“阿菊姐(我外婆小名),去看过小凤啦?”
我外婆抿着手帕纸擦了擦眼角还未风干的眼泪,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们仨刚去了。”娜婆婆刚想继续说点什么,一抬眼看见站在外婆身后的我。她瞬间像切换个频道一样,从苦情剧到欢乐场笑呵呵的说:“哎呀呀,原来是囡囡也回来了呀,瞧我这老太太老眼昏花的,这么好看的一朵花插在这儿我楞是看不见。”说着就准备走过来牵我的手,我呢还自顾在自己的思绪里神游。坐在外婆身边的妈妈戳了戳我手臂,悄悄朝我的说了句:“木头一样干嘛呀,打招呼叫人呀!”然后自己笑着帮我打了个圆场:“我家囡囡啊!从小就得了您几个老太太的照顾那么的疼她。吃了您几个不少好东西,以前小板凳一搬往她外婆小院门口一坐,跟个小土匪似的,小嘴一张一合谁从她面前过都能让她骗点吃的过来。你看看现在像牙齿镶了钻石嘴巴上了锁一样,一开口就怕磕坏了豁了牙哈哈哈哈……让您老几个笑话了哈。”
我有点脸红很抱歉因为自己刚刚神游而失态了。快步走到娜婆婆跟前半蹲在她脚边叫了声:“娜婆婆!我回来了!好久没见您了,您还一如既往的硬朗,真好!呵呵呵我好抱歉呀,回来得匆忙都没买礼物呢。”
娜婆婆拉起我的左手,又像儿时一样捏了捏我的脸颊柔柔的说:“哎呀呀,怎么瘦这样了?工作太辛苦了吗?没好好吃饭?经常犯胃病吗……”像炒豆子一样,一下蹦出了好几个问号,我已经安排不好先回答老太太哪个问号了。只能用一直微笑回复老太太的关心。她看我一直半蹲着在她脚边,想给我找个椅子坐一坐。拉起我右手时候发现了我手臂弯上那条有点像蚯蚓一样的伤疤还若隐若现的印在那里,她轻轻的抚了抚那伤疤嘴里喃喃的说了一句:“阿菊姐啊,十几年了囡囡这疤依然还这么明显,那年囡囡摔断了手臂救下了阿凤,可谁曾想她十几年后还是走了这条路。”说着说着她那不算清明的眼里慢慢起了一层雾气。往事的尘埃也随着这条疤痕的若隐若现轻轻扬起……
我10岁那年的暑假我跟弟弟在外婆家小住,那天的清晨外婆家杀了一头肥猪,她忙忙碌碌的一上午,煮了一锅的肉、肠子、猪血等,她一碗一碗的分好放在土灶台面上,江南的农村有个风俗就是谁家杀猪了就会给周围的邻居每家送上一大碗,养猪脏乱臭给左右邻里带来的困扰与不便聊表一点心意。
那天也不例外,外婆分好后喊我过去说:“阿凤妗妗家虽然就在后面一幢,但她家的厨房在四楼,你去吧!小孩子腿脚轻便你端着送去啊。顺便问问她家有没有苹果带两个回来,外婆给你和弟弟熬点苹果羹。你和弟弟嘴角都起皮了……”
我得了外婆的指令后老早像上了发条的青蛙一样欢乐的朝阿凤妗妗家蹦去,仿佛还能听见外婆在后面喊着,囡囡慢点跑,汤别撒了!我已经蹿到了阿凤妗妗家的四楼楼梯口,楼梯口的门关着我嘴里叫着:“妗妗快开门!我端得东西有些烫。”同时也侧着身子用一边的肩膀去推那个门,原来门是虚掩着的,进了四楼的走廊左手第一间就是厨房,同样门是关着的,我一连叫了好几声“妗妗”都无人回应,心想可能是去田里干活了,那就把东西放厨房就回。因为两手端着碗,我是用屁股跟背去推厨房门的,我刚屁股一撅背还没怎么用力呢,厨房门就好像有人从里面帮我开了一把一样,我差点摔了一踉跄,手里的碗因为身子一晃有些汤就晃荡到手背上,有一点点微疼。我刚想撒娇的抱怨一下下:“妗妗你是在家的吗?居然没听见我喊你,我要生气喽!”
一转身就看见她挂在了锅台边那个大窗户的梁子上小板凳在一边翻着,脚还在蹬。我惊得脑子有空白了几秒,等反应过来第一下去抱妗妗的腿往上举。想试图把她从那绳子套上解下来,但这其实是最笨的办法。力气太小反而加重了下坠力。
我趴窗户上惊叫着哭喊:“外婆救命、外婆救命,快点救命。”
喊完又飞快的冲出去,想跑楼下找救兵。就是跑下楼的时候我是不记得从几楼开始自己是从楼梯上滚下去的。等我到一楼的时候,我小舅舅已经跑过来了问我怎么了?我嘴已经说不利索了,就直接说:“舅舅快去厨房救命,吊在那里了,吊在那里了.……”
小舅那会年轻脑子反应快,速度也快,跑到厨房救下了人。还懂点急救知识,做了一番急救,妗妗活了下来。
后来等外婆她们赶过来时,我小舅已经把阿凤妗妗背到二楼的睡房,正医院再检查一下,外婆看我坐在一楼的台阶上,傻愣愣的眼泪鼻涕糊了一脸,胸前的衣服也洒了一片的油腻面目全非了。正想问我刚怎么了,外婆看舅舅下来了说:“阿卫,怎么啦?你刚像屁股着了火的往外冲。”小舅舅说:“开始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刚停好摩托车就听头顶上囡囡惊叫的声音喊救命,一听是在后面我就跑过来看看哪知……”
我舅舅把刚刚事情大致的跟外婆说了一遍,听得外婆捂着胸口直呼:“阿弥陀佛,佛祖保佑。”
小舅舅看了一眼在楼梯上傻坐的我,跟我外婆说:“妈!先把囡囡带回去喂点珍珠粉吧,她应该吓坏了。”
外婆并没有听从舅舅的先把我带回家,而是她拾一级楼梯坐在我旁边,手在我后背轻轻的抚摸着温和跟我说:“囡囡,你小舅舅说你吓坏了,外婆觉得我的囡囡肯定没有,只是没有见过阿凤妗妗这个样子,有点心疼也有一点不适应对不对?就像上次咱们家的母猪生小猪,她难产了,一只小猪挤在那里都快变形了,开始你也觉得很怕的,后来你见到母猪后面生出来的小猪粉嘟嘟的好看又可爱是不是就又好了?一点都不怕了对吧。你现在也闭着眼睛想想平时阿凤妗妗那笑盈盈的脸喊你去吃红烧蹄髈的样子,是不是你都有点嘴馋了呵呵呵。”
外婆稍微用力的抱了一下我的肩膀继续说着:“囡囡,你啊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也会遇见有很多很多你没见过的让你害怕的场面,但要记住啊,害怕不能放心里,要像吃的东西一样放在胃里,让它消化然后排出去。也要做个好人,心里坦荡荡了,妖魔鬼怪不沾身。还有要多读书哦,多见世面,再没有路了也不要走绝路……”那天外婆就这样坐在台阶上跟我说了好久,我居然趴在外婆的膝盖上睡了一觉,最后是因为手臂的剧疼给疼醒的,原来楼梯上滚下来,我的右手粉碎性骨折了。起先因为恐惧忘记疼痛。
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中途阿凤妗妗来看过我,她来的那天脖颈上还有一圈淡淡的紫色勒痕,恰巧我因为那个骨伤的药吃了胃难受,在跟我家老外婆发“大小姐”脾气,她很内疚因为她做的傻事害我吃了苦头,放下水果罐头后在我床边悄悄的抹眼泪,外婆拉着她的手安慰说:“阿凤啊!没事的不难过哈,小孩子恢复得快很快又活蹦乱跳跟个皮猴似的了,但是阿凤阿你可再也不要想这条路了。”
我至今还记得她当时拉着我外婆的手说:“阿卫妈,我错了死过一回才知道自由呼吸的重要,活着就会有路的。”
可当时的信誓,哪知20年后她还是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结局。
医院走后,外婆并没有告诉我她这次走绝路的原由,而是跟我讲起了她往事。
那是年的阿秋挺着篮球大的肚子跟她的婆婆还在替地主马大富家摘棉花,剩最后一条田坎棉花了,阿秋突然觉得尿急,蹲下没几分钟,一个粉团子就掉在了田坎上。
粉团子哭声不大,但隔着几条田坎远在低头摘棉花的阿秋婆婆听得却异常清晰,她像被渔网困住的大鱼发出了洪荒之力踩断好几株条棉花树挤了过来,中途跑得太快还摔了几次,跑到阿秋脚边一脸兴奋地像喝了尿糖一样,她搓了搓手,把粉团子翻了个身看看究竟是男是女。等看清结果后,刚还因为兴奋微涨得微微发红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甩手把粉团子扔回田坎,她又像一条老鱼慢悠悠的往原先的田坎游去。阿秋脱下自己的外套草草的包起粉团子把她放在田坎上,又继续摘完剩下的棉花,再抱着团子怯生生的跟在婆婆身后回了家。婆婆在前头走得虎虎生风,阿秋走得绵软无力,她知道等着她跟团子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回到家,走在前头的婆婆比阿秋先到家,她黑着一张脸跟她儿子阿甲说,又是个赔钱货,你看怎么办吧?跟在后头的阿秋前脚刚跨进院子,迎接她的就是一只飞行的烟斗狠狠的砸在她的脑门上,接下来就是犹如山洪般的咆哮。
粉团子降生前,阿秋已经生了四个女儿。这次她生下的这个粉团子,在这个恶毒得野狼看他一眼都想上吊的男人眼里,新生命的到来还不如院子里那个老母鸡下了个蛋来得讨喜。阿甲跟他妈说这团子无论如何不能留,阿秋刚想开口恳求,阿甲一个响亮的耳光让她的世界瞬间安静了几秒。等她再次能到这世界嘈杂时,她也并不能像一只护犊子的母狮一样张牙舞爪的跟野狼搏斗,她是懦弱的。阿甲与他老娘骂骂咧咧的进了里屋关上门像两只老乌鸦呱呱呱呱的叫开了。
阿秋想透了,如果现在不抱走眼前的小团子绝对活不过今天晚上,她思索了一下自己有个堂妹阿冬就嫁在隔壁村,抱到她家再另外想办法吧,就这样连夜送去走连。这一走小团子与这个家从此再无瓜葛。
送到隔壁村堂妹家养连近三个月,团子已经会笑了,笑起来还极其好看两凤眼弯弯像极了月牙。所以由此取名月凤。
小月凤在小姨家住到了一岁多,到了年的下旬全国都即将解放,当时阿冬村里有个在富户家里做长工名叫阿满的男人,不是本村人呢,他们有个原先有个儿子长到七八岁的时候有次掉进富户家的水井里淹死里,从此他们夫妻就再也没生养,见小月凤好看又机灵,平时阿满的媳妇就特别喜欢她经常逗她玩小月凤对她也很投缘,年全国都在渐渐的接近解放,农民翻身做主人的的日子马上就到来了,阿满夫妻也一样半生给人做牛马,也像回自己村做回人。临走时提出想把小月凤带走。
阿冬跟阿秋商量以后欣然同意。往后有十几年的日子,小月凤过得如何并阿冬也并不清楚。这一段出生的回忆也在好久好久以后,阿冬都已经老得两鬓斑白、步履蹒跚,记忆也开始需要从远古跋涉时,再一次阿凤接她来小住时才跟我外婆闲话家常才说起。那会已经十年浩劫都已经过去。
其实当时外婆跟我讲这一段时候,我曾问过外婆:“为什么四个都养了,阿凤的爹跟奶奶就不要她。”外婆说:“人与人之间的缘份深浅,前世早已经安排妥帖,缘份深打断骨都还连着筋,缘份浅打个照面就是一生。多一分也不会是因,少一分也不会是果。”
当时十岁的我显然听不懂外婆讲的其中内涵,仅仅是觉得这一句很好听。
阿凤来到我外婆村里的时候,已经是年了。捡到她的时候她昏死在村外一个稻草垛旁,村里的张奶奶家里偷偷的养了几只长毛兔,因为兔子窝太潮了想从集体的草垛里偷抓点稻草回去,刚巧就遇上她倒在那里额头滚烫,喊人把她背回家,又灌下去一大碗姜汤,又盖了厚棉被发了汗她才缓了回来。
醒来的阿凤说着一口湖南方言,张奶奶一家包括村里几乎都没有人听得懂讲什么,当时的人娶媳妇跨个县都会觉都会喊是外地媳妇了,何况湖南到金华那真不少距离。而且阿凤也不认识字,沟通有些许的困难,差不多住了有大半年的日子,才慢慢的了解到,她9岁的时候母亲死于肺痨,在家跟父亲相依为命了几年,父亲也发现得上跟母亲一样的毛病,父亲觉得自己时日不多,准备把她托付给远嫁在哈尔滨的姑姑,姑姑也在那边给她找了个婆家,可是父亲没坚持到哈尔滨在路上就驾鹤归去,走前告诉她,她只是他的养女,她的老家是在金华兰溪,那里有她四个姐姐可能后面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但具体的村庄父亲又没详细说起,所以她安葬完父亲就一路往南奔了,用脚孤独的丈量着大半个中国。
张奶奶心疼着她的孤苦无依,也通过大半年的相处觉得她是好看又善良的女孩子,张奶奶家里有个孙子细亚跟她年纪相仿有意想撮合在一起。奈何细亚心里早已住着本村的村花。
可这也没关系并不影响阿凤继续住在张奶奶家生活下去。有人说红鸾心动时,月老都会来相助所以幸福依然如期而至。阿凤跟村里的男青年阿桥相爱了,白天一起去生产队出工,晚上小溪旁甜言蜜语对着月亮许下一生的誓言。
那时候车马很慢,喜欢一个人就是一辈子。几个月后阿凤娇羞的跟坐在院子里纳鞋底的张奶奶说她想跟阿桥结婚了。奶奶一听开心得一双已经不太清明的眼睛里慢慢放出光来浑浊却温润,从心里祝福她们。可转眼想到阿桥那个妈,张奶奶从骨子里蔓延出一阵寒意,心里打了个冷战。她实在是不太好相与。
阿桥的妈娥嫂,不知道是否因为从小被卖进大户人家做过童养媳,也许在她那从花骨朵到含苞待放的那段岁月里受过非人的待遇,总之她嫁给阿桥爸以来,她在这个山明水秀,风清气朗的自然村落显得“与众不同”。她喜好与人“切磋”、“舌战江湖”。
刚嫁给阿桥爸的时候,阿桥奶奶还在世她还算收敛,因为她听人讲,阿桥的奶奶当年是女土匪出身有功夫傍身。(其实后来听见过阿桥奶奶的人讲,老太太是个很仗义很有侠骨风范的女人)几年后阿桥奶奶过世了,娥嫂像千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彻底的解放天性了,路上谁往她家院子多瞧一眼,她就觉得那人要偷她的鸡,她拎个马扎高耸的颧骨顶着一张褶皱的皮,两眼怒目圆瞪,明明瘦削干瘪的两颊这时却像塞进了两颗乒乓球,以部分人体器官为半径,把那人家里的祖宗十八代全问候一遍。能骂得两边嘴角起飞沫活活的像一只癞蛤蟆。直到对方恨不得自毁双目为自己刚刚多看一眼谢罪,她方才鸣鼓收兵凯旋回家。
其实阿桥并不是娥嫂亲身的儿子,娥嫂嫁给阿桥爸有好几年不曾生养,村里迷信的说法是从外面领养一个,以此先壮壮丁后面就会子孙繁茂的。就是这样阿桥还在月子里时被抱养回来。不过后面娥嫂确实也陆陆续续生了两儿两女。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阿凤觉得她嫁的人阿桥是个好人就足以。年的正月阿凤成了19岁阿桥的新娘。阿凤是在张奶奶家出嫁的,当时张奶奶作为阿凤的半个娘家人跟娥嫂提了个要求,等阿凤生下头胎,他们夫妻俩就分家出来单独过。娥嫂当时嘴上是勉强答应了,可她心里的小九九早就转开了。她自己生的四个小孩最大的也才12岁,她还指望阿桥赚公分养活这个家呢。所以她不会轻而易举就让这对小夫妻分家出去单过的。
婚后的阿桥阿凤夫妻恩爱,日子平稳幸福。只是阿凤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阿凤有些着急,每每阿凤着急时候阿桥就憨憨在边上笑着劝媳妇:让她不要着急,两人都还年轻可能营养不好。嘴巴上安慰着,也会趁农活不多时候去山上抓只兔子河里摸点鱼来给媳妇加一点营养,只是每每这些东西拿回来娥嫂都想尽办法尽量得给自己生的孩子多吃一点。
阿凤也不计较偶尔会说个一句两句,娥嫂就要指桑骂槐的说她不会下蛋的鸡。唉……
(待续。)
亮兄天官赐福!
转载请注明:http://www.qiyacar.com/lyjd/9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