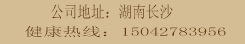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毛里塔尼亚 > 行政区划 > 越过万水千山,探荷西
当前位置: 毛里塔尼亚 > 行政区划 > 越过万水千山,探荷西

![]() 当前位置: 毛里塔尼亚 > 行政区划 > 越过万水千山,探荷西
当前位置: 毛里塔尼亚 > 行政区划 > 越过万水千山,探荷西
不喜与人谈书谈电影,不喜与人分享精神世界,不愿受人指点品味。钟情三毛多年,但并不对人推崇她的精神或作品,觉得深藏心中足矣。近年又掀“三毛热”,关导的影片计划也随之喧嚣,我于私心并不期待,怕是没有人能够完美演绎三毛的一生,再且每个人对三毛的画像不尽相同,影片将形象统一化,扼杀了想象空间。
喜欢三毛,喜欢她的情怀,并不在乎她去过哪里,也未盲目追随她的行迹。惟其如此,这趟来摩洛哥旅行前,对于三毛荷西曾居于此,我的脑子里毫无印象,却又因着三毛的缘故,执着前往阿尤恩一看。
始终认为荷西未必是三毛的最爱,但一定是三毛最契合的灵魂伴侣。他有恒毅,守得起这样一位随时消失的女子,也甘愿为她放弃一切,四海为家。
在阿尤恩的大西洋边上时,与一位撒哈拉威女孩在灿然星空下聊起三毛,提及她自尽,又直言三毛是我到阿尤恩的原因。女孩见我对三毛有同理心,似乎会错了意,以为我也有寻短见的念头,颇显激动,连说自己尊重我对三毛的喜爱,但绝不赞同三毛离开世界的方式。我抚慰她,说自己乐观积极,人生步入任何逆境,都不会自行结束生命。
我惋惜荷西的突然离世,同时也理解三毛为何告别世界:她的人生太精彩,有着堪比百岁老人的经历,延不延续,对她而言意义都不大。但有时我也遗憾,若三毛仍在,或许能感动更多人。
初访拉帕尔玛岛
大加那利群岛是西班牙的海外自治区,也是欧盟最外延的特别领域之一。三毛与荷西曾住在首府大加那利岛上的泰德小镇,而荷西逝世于另一岛屿拉帕尔玛,他的墓碑也在该岛上。我本打算航班落地后直接前往泰德镇,不料问路时认识了选修中文的当地女孩艾礼莎。一聊,艾礼莎的小组研究课题,选的正是三毛。艾礼莎建议我住在拉斯巴马,更热闹也更便利,我听从,结果不出意外地迷路了。忽遇一家中餐馆,进去问路。中国老板一见是同胞,尤其热情,老板夫妇来自福建,已在加那利扎根20余年。我点了炒面,老板娘进厨房,炒锅砰砰几下,捧出一大份炒面给我,足三人分量。
老板一直劝我在他家住下,我答应了。老板娘在忙,我把50欧放桌上,想付餐钱和住宿费。老板娘喊我“小妹,钱别乱放。”我说是付她的,她却固执:“都是中国人,不用给钱。”我坚持付饭钱,老板娘象征性收了5欧,尽管餐牌标着10欧。
老板娘把我领回家,给我钥匙,指着房门对我说:“你晚上如果怕,就反锁房门,我和孩子们住这里,不会对你有什么企图。”分明是她领我这个陌生人回家,不仅不怕我使坏,还交代我别害怕。
老板娘说,西班牙现在经济低迷,以前在加那利,沿街乞讨的都是隔海而来的摩洛哥人或吉卜赛人,现在竟也有了西班牙本地人;他们夫妇的店铺主要经营酒吧,也做中餐,经济形势倒退,他们的生意大不如前。“我挺累的,也好想像你一样旅游,可是旅游也很累,再说我们的西语仅限于点菜,也不会英文。我们每天5点多就要起床备菜,夜里1点多才收店,暂时关了店去旅游吧,心又放不下。”老板娘一边说,一边困乏地打哈欠。
遗憾的是,从这次交谈结束到我搬出,都没再见到老板夫妇。当天西班牙皇马主场,酒吧生意颇好。我想亲口对他们道谢,无奈等到夜里4点仍不见其归。我觉得酸楚,深明同胞的勤劳来自血脉,也是祖国愈加强大的原因,可看着街上店铺都因周末而歇息,唯独中字招牌的店铺还亮着灯,里面是为了孩子为了生计而奔忙的同胞,我心有矛盾情感。
抵达拉帕尔玛,到旅馆放好物品后第一件事是去买花给荷西,不料周日市场店铺一律关门。见街头一位漂亮的西班牙女孩手中有两支玫瑰,便前问在哪买的。女孩娇羞地拉着身边男孩,“男友送的。”
买不到花,我难过。女孩问我怎么不第二天再买,我告知因赶着去祭拜一位亡友。女孩一听,毫不迟疑地立马把玫瑰塞到我手中。我也没再客气,谢过灵魂与外貌一样动人的她。
玫瑰还带着朝露,想必荷西会欢喜。别过女孩,我总算走到墓园,可因是周末,墓园闭门谢访。
既然闲着,便在城里乱逛,这一逛,实在不得了:拉帕尔玛太美!来之前,西班牙朋友都嫌弃,说我怎么挑了个又小又偏的岛旅游。可这一看,山河海湖,银河星宿,火山植被,拉帕尔玛岛应有尽有,风光明媚。后问路遇见的中餐馆老板来自福建,见是同胞,老板尤其热心,提供旅游资讯之余,又连问要不要吃喝。老板遗憾地说他翌日要外出,不然一定开车载我环岛。后来在拉斯巴马和拉帕尔玛都遇到不少热心的华人店主给指路或是邀请吃住,在这微丝细眼棉干絮湿之中,我尤感到作为同胞的欣喜和感恩。
(拉帕尔玛一隅)
夜半到山顶观星。来了拉帕尔玛岛才知道,由于地处大西洋信风带,这里常年干旱少雨,晴朗的天空有利于清晰地观测夜空,而岛内海拔米高的查乔斯岩火山上还建有一座世界闻名的大型天文台。载我上山的司机告诉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天文摄影师每年夏季都会来岛上,租他的车子上山拍摄银河,就连见惯美景的他们,也常常被这里的银河所震撼。
车子一路朝山顶开,愈加远离市区光害。窗外,银河挂在苍穹,漫天星斗散落如棋,忽明忽暗。我努力抑制住尖叫,身旁的司机却说:“因为有雾霾,今晚的星空很一般。”他口中的“雾霾”,指的是撒哈拉空气层带来的沙尘。他笑言:“每次有沙尘,就说明对海摩洛哥的骆驼又开运动会了。”
(当地司机口中“一般”的当夜星空)
(被加那利这“一般”的星空震撼许久)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梳妆打扮,想着这辈子可能只见荷西一次,不该随意。进墓园后,把荷西的西语全名给工作人员看,他只消看了一眼,便读懂我心似的,一路领我往里走。
我曾劝诫自己,无论荷西的墓多荒芜,甚至碑牌可能年久失修,都不要哭,不要文艺腔泛滥。可当工作人员往墓碑一指,我傻眼了:墓碑修葺一新,开了一个透明小柜,供悼念者在小石头上留言,小柜里放着三毛荷西合照,墓前放了好几束鲜花。墓的两旁,一边是关于荷西的悼词,一边是花坛,放了三毛荷西照片。原来,有这么多人千里迢迢地为三毛荷西而来,我的泪刷刷不止。
(荷西的墓碑铭牌)
无论之前我多么理解三毛的离去,那一刻我开始责怪她:这么多人爱你,你怎舍得走。
荷西的简介里写着,他生于年,卒于年,可见是比年出生的三毛要小8岁。而三毛在书里说荷西比她小4岁。可爱的三毛,浪迹天涯个性洒脱,却还顾忌着亚洲社会的世俗陈见。
动手去清理荷西墓前满放着的花束,取走枯萎的那部分。水池就在不远处,一旁备了十几把薄荷绿的铁壶。取一把壶,灌满水,为花束润了喉。难以想象当年痛失丈夫的三毛,是如何做这一切,想必抬手迈步都揪心撕痛。
墓园职员贴心,见我还在,给我递来钥匙和记号笔,让我开柜取石子留言。
于是写下了:
旅途遥远艰辛,于我并不打紧,只要见到你们,就是旅程意义所在。在我彷徨的岁月里,《温柔的夜》点亮了我的人生。你们点醒我:世间除却金钱、权力、竞争、攀登,还有善良、自由与真爱。
相信你们早已重逢,在那无尽的透明过道里。
有空梦里相聚,说说新的旅途故事。
只是,
笨蛋荷西,拜托这辈子别再潜水啦;
傻瓜三毛,拜托这辈子活久一点呀。
很想你们,
怀念你们,
感激你们。
(荷西故去海域)
离开时已是正午,墓园里温暖光亮,没一丝怖惧之感。荷西歇息处,山清水秀,让人欣慰。墓园东边,对着的正是荷西热爱的那片大海,海面波光粼粼。整个世界静悄悄,一如一切生离死别都没上演过。
与南施姐结缘
朋友玺哥热心,知道我喜爱三毛,约好了三毛生前好友张南施与我见面。在《随风而去》里,三毛曾写“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
见面前,我心里有很多顾虑,怕打扰了南施姐的私人空间,更怕的是,南施姐借三毛名气盈利。
见了面,才知道自己怀的是小人之心。我和玺哥不必敲门,南施姐闻电梯声,早早打开门来。她探出半个身子,笑意满盈,不问来处,不问意图,只如故知一般招呼:“来啦!”
南施姐13岁时初见三毛,她说,三毛不“嫌弃”她人生经验少,纳她为友。才见南施姐,已深明三毛为何偏爱她:她亲和,在加那利的经商经历和丰富的人生履历,并没有叫她挑起眉梢瞧我;她打扮简单却大气,短发和干脆个性很相衬,是叫人看一眼便觉舒服的气质。
三毛,好眼力。
与南施姐、玺哥聊了大半日,自有落泪处,但因涉及三毛等人隐私,这里只截录几个触动心灵的部分:
我私下忖测,觉得荷西是脑子简单的大男孩,夫妻俩在撒哈拉的生活,经济来源大多靠三毛的稿酬。南施姐却告知,荷西是个目标清晰的人,他少时立志要挣钱,梦想是“做个百万富翁”。他去打工,在餐馆、面包店都工作过,这对于大多数爱玩的西班牙孩子而言,并不寻常。荷西十六七岁时,就爱上了三毛,他对家人说自己要努力挣钱,“要娶老婆”。
初见三毛,荷西还在念高中,后来荷西升入大学,修读机械专业。荷西对航海有狂爱,后来又钟情潜水。毕业后,他参加部队里的潜水工程师执照考试。当时统共50人报考,荷西得了最高分。待再见三毛时,荷西已有高级潜水工程师执照,觉得自己“有养老婆的能力了,可以找工作了”。后来,听三毛说起喜欢撒哈拉,荷西不声不响地去了撒哈拉,把工作找好,等着三毛过去。
我在阿尤恩看到的三毛荷西的故居,房子破旧,通风透光情况都不好,当时猜想,三毛荷西在阿尤恩的日子并不好过。后来到了加那利群岛,对各岛的地理位置有了了解,再想起三毛住在大加那利岛,而荷西却在偏远的拉帕尔玛岛工作。夫妻分居两地,想必也是为生活所迫。
但南施姐都否认了,她解释,当时在西撒哈拉,驻外人员一般会挑选环境好的社区来居住,既为安全,也为生活质量;三毛荷西却选择了更便宜的住处,甚至临近坟场,是因为小夫妻精打细算过日子,省下钱来,为未来规划。
当时,西撒哈拉是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年,被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认定为接班人的西班牙政府首相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被埃塔组织安放的汽车炸弹炸死。而在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重病在床,已无暇顾及西撒哈拉殖民地。西撒哈拉,是继续由独裁掌控并由军人接政还是独立,无人能准确预测。南施认为,即便是在现今的西班牙,有良知的国民仍觉得西班牙亏欠西撒哈拉人民,并没有扶植好西撒,导致最后让撒哈拉人和平进军。
终于在年11月,摩洛哥政府发起大型群众游行活动,即“绿色进军”(GreenMarch)。其时,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号召起35万非武装的摩洛哥平民,由政府组织和军队保护,从摩洛哥南部城市塔尔法亚出发,举着代表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越过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之间的分界线,以迫使西班牙放弃对西撒地区的控制权。因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重病,西班牙无意在此时卷入战争。一周之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匆忙签订《马德里协议》(MadridAccords,也称MadridAgreement),承诺在次年初从西撒全数撤军,放弃西撒殖民地。
殖民地前途未卜,安全成问号,作为外来者的荷西与三毛同其他外籍人员,也决定撤离。他们选择了离撒哈拉最近的西班牙领土,即加那利群岛。大加那利岛是加那那利群岛的首府,因此所有驻外机构都选址在此,加之交通较其他岛屿更便利,三毛夫妇便选择了定居大加那利岛。
(如今的大加那利岛已成旅游胜地)
三毛先独自乘班机前往大加那利岛,荷西由于有工作任务在身,是西班牙人里最后一批乘船离开撒哈拉的。不同于我的猜想,荷西前往拉帕尔玛岛工作,是因为水底工程工作移动性很大,地点不固定,哪里有工程,荷西就往哪里跑。除了拉帕尔玛岛,荷西还曾前往非洲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等参建工程。由此看,荷西对家庭亦颇有经济贡献。当然,三毛当时已是台湾版税最高的女作家。南施姐却告知,在西班牙朋友圈子里,三毛从未炫耀自己的作家身份,她的西班牙朋友甚至不知她是作家,更别说知道海的那头已掀起“三毛热”。
南施姐回忆说,三毛对荷西感情很深,每次荷西前往外地工作,不出一个月,三毛必定前去探望。那时荷西在拉帕尔玛岛,一旦稳定下来,三毛就锁上房子,驾着小车,开上渡轮去看望荷西。后来荷西去世,三毛回台湾,任教于文化大学,却仍如候鸟一般,每年回加那利度假及探望好友。直到年,三毛对南施说,父母年纪已大,她想回台湾长久待着,陪在父母身边。
南施姐继续打消我的忧虑,她说三毛爸爸曾是律师,家境很好,而三毛是个毫不在乎金钱的人。在年,出国仍是奢侈的事,三毛却能到西班牙去。她又举例,荷西逝世后,三毛得到一笔“寡妇抚恤金”,金额颇大。当时,因为荷西家人与三毛有遗产纠纷,三毛将房子急急转手,卖给了西班牙人璜。璜并未更换家里的号码,仍用着三毛(EchoChan)的号码,而每月30欧左右的电话费,从三毛的寡妇抚恤金里扣除。三毛对此从不在意,可见经济条件不拮据,也可见其从容的金钱观。可直到三毛逝世,璜仍在用着三毛名字注册的电话号码,并享用着三毛的抚恤金。璜自辩这是三毛与他的约定:不必更换号码、名字。
三毛逝世后,其家人抵加那利群岛处理遗物。璜淡淡地提及抚恤金一事,让三毛家人考虑如何处理。三毛家人忆起,三毛曾替邻居甘蒂在大加那利一家学校代课,家人去校区看过,认为教学条件并不乐观,于是建议将抚恤金捐给学校,希望改善教学环境。三毛对金钱物质的洒脱,可见传承于此。
不仅是璜,在三毛离开后,打着她名号来哗众取宠、赚钱获利的人不少,诽谤她名誉的人也不少。正如同南施姐所说:“爱护三毛的人很多,伤害三毛的人很多,利用三毛的人也很多。”
我忍了很久,曾打算不提痛处,最后还是问及了三毛的离世。南施姐说了很多,内容如同读者们了解的那样,在三毛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她过得很累、压力很大:教书、演讲,加上被出版社催稿的压力,让她很难过。
年6月25日,在给南施的最后一封信里,三毛语气悲凉:
“前年、去年我常在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一带,去年我开始回中国。上个月方自新疆回来(去走丝路)。下个月我再去北京以后,转去青海,预计去三四个月,一个人走。
去年将肋骨摔断,插到肺里去,也开了肺,苦了半年左右不能好,一好,就去了丝路。在这儿,我也很少跟西班牙朋友来往,我去年住院时,一个西班牙朋友去看我,我们讲讲西班牙文,我就哭了,他说:‘不要哭了,好了还是回西班牙去吧,我们合租一个公寓生活也便宜些。’事实上,这些都已是梦话,南施,人,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我也很难再回西班牙去了。明年我想回西班牙一次,当然去拉斯巴马,也许冬天再来了。
这么写信,对于西班牙的想念就更强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相处,充满了感情和真诚,这种情感,在中国不是没有,也有的,可是整个社会风气,口气,却不是如此,而且人不真诚。
南施,我有好多的话想讲给你听,可是现在不惯写长信,又想,你有餐馆,有咪咪,有小强,有父母,忙也忙够了,看我的心事实在不必。”
半年后的年1月4日,三毛自缢身亡。
三毛的兄弟姐妹都后悔,当初不该让她卖掉加那利的房子,这无疑断了她的后路。她在台湾压力大,但避无可避。
但三毛妈妈不认为这些压力足以让三毛离世。南施姐说,陈妈妈坚信,三毛不是自杀,而是心脏衰竭死亡——三毛体质弱,心脏一向不好。陈妈妈回忆,三毛压力大,常失眠,夜里睡不着,就起来做家务。三毛爱干净好整洁,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收拾,也成了三毛暂忘失眠的良方。但后来三毛因子宫内膜增生症,医院接受治疗。陈妈妈分析,医院里没什么物品可供三毛清洁,夜里睡不着的三毛起身不知该做些什么,于是去洗丝袜。病房里有钉在墙上的点滴架,三毛洗好了丝袜,挂在点滴架上想晾干,可就在那一瞬,她心脏病突发,瘫坐在马桶上,脖子正好挂在丝袜上。
这样的分析,细想起来应当不仅仅是一位母亲的自我慰藉。我搜寻图片,医院的点滴架,看起来并不承受力超凡。南施姐说,三毛与她体重相当,大概50公斤,即便不重,也不是一个点滴架可承受得起的。加之,人自缢身亡,会痛苦,甚至会后悔,更有可能因此挣扎,但三毛毫无挣扎痕迹,表情平静安详。再且,自缢离世,常理应是悬挂身子,但三毛走时坐在马桶上。只要她后悔,稍微站起身即可。陈妈妈坚信,三毛不会自尽,理由很简单,“她答应过我们,不会走在前面。”
我问南施姐,陈妈妈有没有将此见解告知媒体,南施姐惋叹,当时台湾的死亡报告明确写着“自缢身亡”,加上许久前三毛的德国未婚夫心脏病发离世,三毛曾割腕自杀,手腕上的伤痕,一直用手表盖着,家人便没再深究。
在荷西的墓碑一旁,有这样的悼词:“这些岛屿不再是他们的人生天堂,意外成为他们的坟墓。水、地,尤其是每个冬季的阳光,连接所有的生命充斥了他们的遗体。前葡萄牙航海员行程、拉帕尔玛岛美岛及台湾宝岛因此一线连接的记忆:人、海、和平。”
(荷西墓旁碑文)
这段话由拉帕尔玛岛一位本地作家写就,说是作家,实不恰当,他是拉帕尔玛岛文化局的一名记事官。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远赴拉马尔马岛,为的就是看一眼荷西生活和逝世的地方,这现象引起当地旅游局和文化局重视。年5月,当地政府出资,在荷西故去海域旁建起“荷西纪念广场”;同期,未曾见过三毛荷西却对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兴趣的这位记事官,通过走访记录,集成了一部《橄榄树与梅花》(西语书名:ElOlivoYLaFlorDeCiruelo),以西班牙常见的橄榄树喻荷西,以梅花喻三毛,记述了三毛荷西在拉帕尔玛岛的人生最后光阴。
墓碑悼词由记事官用西语写作,想必是借用了网络翻译,才语法不通。我问南施姐,“前葡萄牙航海员行程、拉帕尔玛岛美岛及台湾宝岛因此一线连接的记忆:人、海、和平”这一句该作何解,南施姐答,三毛与荷西的逝世有很多相似处:他们都在年轻时告别,他们都离开在海岛。
早在16世纪中期,葡萄牙航海员来到台湾,惊叹地叫着“IlhaFormosa!”意为“美丽的岛屿”。因此,台湾岛在早期也被欧洲称为“福尔摩沙”。而荷西意外故去的拉帕尔玛岛,西语别名是“LaIslaBonita”,同样译作“美丽的岛屿”。冥冥中的凑巧,叫人叹惋。
陈爸爸、陈妈妈只见过荷西一次,这一次,即是永别。我身边有朋友好奇,三毛与荷西成婚数年,为何一直不见三毛父母,算否不孝。南施姐却很理解:那时机票价格高昂,飞台湾需要20万台币,以当时加那利群岛的人均收入水平来说,人们需要工作4个月、不吃不喝,才付得起一张单程机票。于是经济条件更好的三毛父母藉着中秋节,前来探望女儿女婿。后来,三毛与父母一同飞往马德里,送爸妈回台湾。那是个周末,荷西与朋友外出游泳,身子被卡在礁石之中,求救不得,遗憾离世。三毛与父母得知噩耗,当即从马德里赶回大加那利岛,由于机票售罄,三毛是同飞机驾驶员一同坐在驾驶舱返回的。
陈爸爸陈妈妈遥遥万里,前来探望女儿女婿,却意外面对如此大的苦痛。大家都坚信,如那时陈爸爸陈妈妈不在身边,三毛心理上必定熬不过这一关。
见三毛悲切,三毛弟弟曾悄悄问南施,“三毛荷西,以前在岛上真的快乐吗?”
真的快乐。南施姐回忆,且不说荷西在世时,三毛与荷西恩爱情深,邻里互重,没有生活压力;荷西离世后,三毛再回大加那利岛,只要一封书信、一通电话,邻居就赶去机场接她。“大家都很爱护她,每天去她家里闹她,争着带她吃饭,请她喝酒,不放她回家,就怕她寂寞难过。
(南施姐家中的三毛旧照)
玺哥打趣我,说我这趟去了撒哈拉,见了三毛故居,又到了加那利,总算触到三毛生平,知道三毛荷西不是假的啦。
然而我从未质疑过三毛笔下故事的真伪,一来我爱旅行,也有奇遇,那些叫人惊诧的故事,在我看来都是旅途寻常;再者,三毛荷西是真是假,三毛笔下的故事有否加入文学性修饰,毫不重要,我、我们、千千万万的我们,爱得真切的是三毛传达的善良与真诚,而这种善良与真诚,是我们人生里的一盏明灯,于浓沉迷沌的雨雾阴森里,照亮我们心灵该前往的路。
这趟旅行的意义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原本该有的意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三毛荷西和他们的故事终究是故去了,三毛之后,世间再无三毛;荷西之后,世间亦无荷西;而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受教于他们的爱与良善还在继续,且生生不息。
(图文皆节选自《我不允许你独自旅行》,有删节,成稿于年5月)
作者
马嘉骊
Carrie
一个旅人,心不思乡胃思乡
马嘉骊Carrie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qiyacar.com/xzqh/3447.html